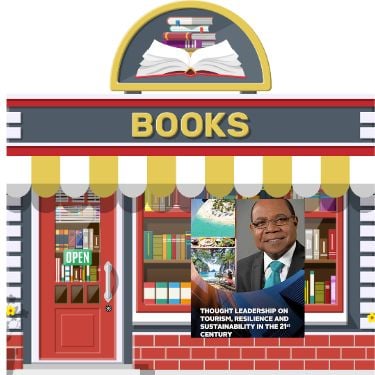- 當洪水來臨時,田地、房屋、公共基礎設施和人類生計被毀壞,遠近的志願者紛紛為慈善事業提供幫助。
- 人們全心全意地捐款。
- 在被野火蹂躪的地區,勇敢的消防員,往往與火風暴的威力相去甚遠,日夜奮戰,直到筋疲力盡。
突然間,自負、享樂主義和舒適區,否則會被視為不當行為的跡象,感覺就像被驅逐,讓位於愛鄰居的願望。 大災變創造了它們自己的法則。 和平時期有英雄,在危險和災難的時刻,人們可能會展示他們的另一面——這可能是他們最好的一面。
任務很艱鉅,挫折是真實的,但樂觀是至關重要的。 緊急緊急情況很容易首先觸發——而且是快速的——援助,而逐漸變得致命的事態發展卻使人們沒有充分意識到引發迅速行動。 逐步獲得的資產將需要時間來開花結果,而冠軍的個人機會“閃耀”正在等待中。
一般來說,和平時期和不太緊急的情況下的英雄主義可能不那麼引人注目,但同樣有價值(“英雄和平主義無疑是可以想像的,”說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和平不是自我表演者; 和平是我們行動的結果。 毋庸置疑,這對作為傳播專家的旅行和旅遊高管採取行動提出了真正的挑戰!
作為旅行者,我們為假期付錢。 這意味著我們更喜歡享受假期,而不是為此付出的代價。 我們應該知道做主人的客人的特權。 社會行為是共存的關鍵。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作為東道主——覺得我們對遊客的熱情好客有可能最終成為陌生人的敵意接管,那麼我們的社會自信心就會受到嚴重侵犯。 製造違規和不和諧是造成環境污染的另一種方式。
我們需要提高對環境意識和人類同理心的“眼睛”,以便了解什麼對我們的身體(外部)和心理(內部)“環境”都有益。 和平只有深深植根於我們作為個人的內心,他們彼此分享尊嚴感。 Travel & Tourism 為好的或壞的做法提供了全球舞台。 有人曾經說過,它就像看不見自己的眼睛。 它可能會學會將自己的觀點對環境敏感,類似於攝影師不斷發展的才能。
看看旅遊業促進國際理解的高調宣稱,我們可能會發現:最壞的情況是假的(例如,包羅萬象的旅行!),最好的情況是一廂情願。 它助長了利益相關者共同的神話,即偏見會消失,並激起我們自己和旅行者共同的沉默希望,即這不會發生,我們可以堅持我們的標準化意見。 我們遇到的不是當地人,而是同胞。 對國際理解的預期自下而上的影響很小:儘管參加觀光旅遊,享受主人的烹飪藝術或瀏覽色彩繽紛的購物商場,但大多數假期接觸只是零星和隨意的。 它們會隨著時間而消失,就像旅行刻板印像有時一樣。
“Tourism Unlimited”的外觀之所以出現,是因為以前非常獨特的社會標記已經變得模糊或完全消失了。 曾經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度假勝地現在在任何目錄或網站上都有提供。
一些地方經歷了特別驚人的轉變,例如巴登-巴登:以前被譽為“歐洲的避暑之都”,富人和美女在那裡舉辦自己的“名利場”,如今的溫泉城市是療養和療養的場所。甚至為福利客戶提供健康。 – 或者選擇馬德拉,在那裡,世界上流社會曾經在氣候溫和的傑出療養院中康復:今天,這個島國是遊輪和旅行團的目的地。
更重要的是威尼斯的情況:威尼斯被列為聯合國世界遺產,直到最近才被來自強大遊輪的短期遊客入侵,威脅著潟湖城市的結構本質和當地人隨和的寧靜。 當地人將這種入侵視為對他們的城市和社交生活的攻擊。
其他地方的情況看起來很相似:吳哥,曾經是高棉國王光榮的印度佛教寺廟城市,從 15 世紀開始衰敗並被遺忘。 人們相信氣候變化(!)和人類的狂妄自大導致了吳哥的垮台。
直到 19 世紀,法國探險家才發現了遺跡,並將吳哥帶到了白天。 在越南戰爭之後,共產主義的紅色高棉征服了他們。 今天,紅色高棉已經消失,“成群的猴子和遊客”(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重新征服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吳哥窟和吳哥城寺廟遺址。
在“旅遊擴張”中,旅遊調查與監測組 (tim-team) 的 Anita Pleumaon 女士總結道:“強加於快速發展的亞洲社會的現代價值觀似乎造成了特別嚴重的破壞性影響和混亂感,異化、動盪和不確定性。 商業化和同質化的過程以及新思想、圖片和信息的大量傳播,給傳統、文化表達、家庭和社區的價值觀留下了很小的空間。” 由於其邏輯和方法論遵循西方模式,我們的目的地方法是否是一把雙刃劍? 我們令人信服的“目的地建設”努力與冷戰後的“國家建設”概念之間是否存在共性?
西方民主與國家建設不協調的最殘酷證據可以在阿富汗目睹。 阿富汗在 1960 和 70 年代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旅遊目的地和歐洲輟學者的天堂,它成功地為兩個世界大國的失敗奠定了基礎:1989 年的蘇聯軍隊和 2021 年 9 月的美國領導的北約軍隊。蘇聯,阿富汗只是一場權力遊戲,對美國和北約來說,它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確定中心和 11/XNUMX 頭號恐怖分子奧薩馬·本·拉登的藏身之處。
美北約軍事干預的目的是推翻當時的塔利班政府,抓捕本拉登。 兩個任務都完成了,但更光榮的挑戰吸引了西方聯盟“留了一會兒”,以鞏固阿富汗作為西式民主國家的地位。 這一目標可恥地失敗了,塔利班農民民兵返回並迫使美國和北約離開阿富汗哈魯姆斯卡魯姆——許多人死亡、受傷或受到創傷,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留下了嚴重的疑慮。 他們最終提出了一個永恆但仍未得到解答的問題:為了什麼?
越戰的陰鬱回憶又重新出現。 1975 年乘坐直升機從西貢屋頂逃生的壯觀照片與 2021 年的照片並列,與喀布爾機場的空中纜車的照片並列,那裡擠滿了絕望的人,其中一些人緊緊抓住飛機的起落架並墜落……
誰有罪? 誰承擔責任? 吸取的教訓呢?
責任在於那些無法理解或拒絕接受他們早先應該學到的教訓的人:第一,社會模式和社會生活方式不能通過武力轉移到他人身上——在阿富汗無處不在,根本沒有; 第二,軍隊的職責是打仗,而不是建學校、醫院、挖井; 第三,軍事和民用項目都需要一個嚴格而及時的固定願景,或者說目標必須是每個人的事業——而不僅僅是具有開放性和許多崇高幻想的善意程序; 第四,地方精英與外國合作夥伴之間的交織關係有進一步加劇裙帶關係和腐敗的強烈傾向。 這種“接二連三”必然會引發衝突甚至戰爭,最終造成赤裸裸的混亂。
很多時候,在三心二意但長期的軍事承諾之後,外國夥伴的最佳選擇似乎離開了情景——反復經歷可恥的飛行,而不是有序的離開,但現在希望得到的主要教訓是:保持排除其他國家的內部問題,尤其是在社會文化差異難以迴避的情況下。 英荷作家伊恩·布魯馬 (Ian Buruma) 提到,當時和現在,大國都容易陷入“殖民陷阱”。
將“殖民陷阱”論點也應用於發展援助非政府組織是否過於牽強? 發展援助面臨的反對主要針對許多技術項目的常年性質,目的是高瞻遠矚,但只有很少的實際結果。 誠然,外國專家不僅可以作為實際的支持者和培訓者,而且可以作為相互競爭的當地利益集團之間值得信賴的調解人。 旅遊發展在其不同的內容和參數方面絕非例外。 唉,一個人過多地參與東道國的內政的誘惑是真實的,而專家的離開可能只是想像他或她已經成為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
通常,由於對“旅遊”和“恐怖主義”在詞源上的共性具有諷刺意味,所以發音清楚是非常受歡迎的,含糊不清可能是致命的:旅遊熱愛自由,恐怖主義需要仇恨。 旅遊業,在其最消極的表達方式中,可能會溫和地扼殺當地文化,而恐怖主義則是立即扼殺,有針對性的和隨機的,毫不留情,但旅遊業是它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旅遊業無法繁榮,恐怖主義肆虐,旅遊業需要和平。 我們怎麼能說旅行和旅遊業有效地促進了創造和維護和平? 有沒有人聽說過旅遊組織與其他組織共同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努力使阿富汗成為一個和平甚至寬容的國家和旅遊目的地,就像它在六十年代一樣?
戰後大約二十年後,越南已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共產主義政權(!),以及與美國和世界的友好關係。 政治談判、商業公司的網絡以及克林頓總統 2000 年的歷史性訪問使政府和商業部門關係正常化成為他們的口頭禪。 Travel & Tourism 緊隨其後,但之前的步驟可能表明了 UNWTO or WTTC 很難回憶。
我們能否將越南視為與阿富汗酋長國關係“正常化”的大膽藍圖? 我們是否可以期待在 2040 年代左右在興都庫什山再次進行冒險的山地旅遊——伊斯蘭塔利班作為友好的導遊?
有人可能會搖頭認為,這太瘋狂了——越戰後的二十年裡,塞繆爾·P·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出版了他的政治大片《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的理論,即未來的戰爭不會發生在國家之間,而是文化之間,這引發了有爭議的討論——以及“文明間對話”的複興,奧地利哲學家漢斯·科克勒在 1972 年在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被遺忘了。
目前的情況難道不能證明旅遊業及其高峰組織的積極干預是正當的嗎? UNWTO 和 WTTC,通過類似的和數字媒體,以明顯而有力的方式幫助更新“文明”之間的對話,代表“通過旅遊實現和平——儘管不僅如此”的想法?
該信息要求在旅行和旅遊業內部和外部加入志同道合的合作夥伴,以集中思想和行動。 它可以受到 Louis D'Amore 理想主義和熱情地傳播和捍衛的想法的啟發國際旅遊業和平研究所.
好吧,讓夢想成為樂觀主義者的特權,而諷刺是弱者的武器——強者有他們自己的問題:當俄羅斯熊從自己的“阿富汗”經歷中恢復過來並重新調整自己時,美國之鷹和它的跨大西洋蜂鳥仍在忙於舔舐他們失敗任務的傷口。 中國龍不能不沉溺於其全球競爭對手的恥辱的邪惡笑容。 世界似乎馬上從冷戰滑向冷和平。 這僅意味著停戰,但足以冒著“熱”政治氣候變化的風險,可能不是沿著亨廷頓的文化“斷層線”,而是大致沿著古老的、熟悉的東西方分界線。 正如哲學家萊布尼茨所說,政治盲目可能引發“源於事件回歸的模式——但僅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想法很難被忽視。 自從鐵幕消失後,政治創造力是多麼的破產啊!
這些模式還有另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論點:“當人以土匪的身份進入世界時,世界將迫使他繼續以土匪的身份生活。 這是世界的回應,我們可以說,這是它的報復,”路德維希·福舒勒 (Ludwig Fusshoeller) 在《Die Dämonen kehren wieder》(《惡魔歸來》)中說道。 被視為入侵者的訪客將被視為入侵者,無論是普通遊客、外展商人——還是外國軍隊! – 我們能說什麼? “再見,歡迎文化”是不夠的。
在歌德臭名昭著的戲劇中,浮士德的真正目標是由他個人戰勝自然決定的。 然而,正當他為完成以自我為中心的計劃感到無比高興時,他輸掉了與墨菲斯託的賭注,並懇求道:“那麼,到了我敢說:‘等一下! 你真可愛!'”
如果我們今天看看我們的星球,我們會發現“浮士德世界”已經公然回歸,而輝煌再次裝扮了昔日迷人的海市蜃樓和東道主和遊客的永恆渴望,並輔以流行病的纏綿詛咒—— “再呆一會兒……”
作者, 馬克斯·哈伯斯特羅, 是創始成員 World Tourism Network (WTN).